起源问题的提出与旧说辨析
出土实物的形制与年代再判断
博山大街琉璃作坊遗址出土器物较多,除石范、陶范、坩埚、剪、镊等各种制作工具外,也有大量琉璃制品(图2),包括管珠、圆珠、楞珠、帽饰、佩饰、围棋子、簪(图3)、笄等10余种,这些琉璃制品一部分存放于博山琉璃博物馆,一部分被淄博陶瓷琉璃博物馆等相关文物部门收藏。所有制品中,簪和钗最能体现时代特色。两馆所展示的琉璃簪外形多呈圆形,也有少部分为方形,簪头则有平头、弯头、花朵形、蘑菇头等多种样式。“所谓平头指簪头端面为平面,与簪体成90度或略斜,流行于宋代”[7]。

图2 博山大街琉璃作坊遗址出土的琉璃制品
(博山琉璃博物馆藏)

图3 博山大街琉璃作坊遗址出土的琉璃簪
(博山琉璃博物馆藏)
一个时代的工艺品与这个时代的社会风气息息相关。如汉魏时期奢靡之风甚盛,加之这一时期琉璃制品尚未在社会层面普及,还独属于上层阶级所用,是以其整体特征是形制丰富、制作繁杂,且花色多样,与宋朝时期的制品有很大不同[8]。而明朝时期,琉璃技术已经在民间非常普及,颜神镇(今博山区)已发展成为当时的琉璃生产销售中心,生产的琉璃制品已有穿珠之属、实之属、空之属3个大类20余个品种,“佩玉叮当,连珠缀缨,绛纱作盛,弁冕盈廷,乃球锵鸣”,制作工艺极为精良,孙廷铨誉之为“以称国工”[9]92,与宋代琉璃制品相比,不仅在类别上丰富许多,在技艺方面更有质的跨越。
再反观琉璃作坊遗址出土的这些琉璃簪、钗,其整体以蓝、白为主。“宋代朝廷重视祭祀之礼,具有遵循古制的时代氛围,官窑瓷器尚青白二色。因而宋元时期的玻璃器,最常见的也是白与蓝。”[10]因此,仅从主体颜色上讲,这些制品与宋代琉璃作品的主色调基本一致。从外形上看,这些制品通体素雅,典致脱俗,与宋朝崇尚简朴雅致之风较为吻合,是以淄博陶瓷琉璃博物馆在对上述制品进行时代注释时,均定为宋代[8]。
纵观各地出土的两宋时期的相关制品,也均有明显的上述特征,如安徽潜山梅城镇太平村的宋乾德四年(966年)墓葬中出土的琉璃簪,江苏南京雨花南路邓府山17号南宋早期墓葬出土的琉璃饰品,以及宋咸淳年间史绳祖墓中出土的琉璃簪[7],与博山琉璃作坊遗址出土的琉璃制品在颜色、形状等各方面几无二致。
陆锡兴在《宋代以来的琉璃簪和琉璃钗》一文中写道:“淄博琉璃作坊遗址时间的上下限是根据文化堆积来确定为金元时代。它出于三层文化层的第二层,第一层是近代扰土层,第三层是金元文化层,有宋‘至和元宝’和‘元□□宝’钱出土。其所出实物有的与北宋后期墓葬出土相似,早于目前估计的作坊遗址年代,不能排除不是该遗址的前期制品。至于琉璃作坊的时间下限,恐怕也不止是明初。”[7]
其实,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相关专家对该遗址出土的琉璃制品进行过科学检测。较早时期的易家良在对该遗址琉璃制品进行化学分析后,就明确表示:“该工场的形成,应上溯到更早世代。”[11]2025年,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挑选36件相关琉璃制品进行检测后得出的结论是:“博山琉璃制作历史可追溯至元末明初甚至更早。”[12]上述研究基于严谨的科学态度,并未对博山琉璃的起源界定上限,但都提到博山琉璃的起源应该比现行界定时代要早。
另外,博山生产陶瓷的历史至少可以确定到北宋时期或更早,这时的博山地区就已经可以烧制精美复杂的宋三彩陶瓷器物[2]97-98,而这些器物表面所施色釉在成分与工艺上与琉璃制作基本相同[13],这也是人们通常将表面施以各种釉色的瓦称为“琉璃瓦”、将低温釉陶烧造窑厂称为“琉璃窑”的一个原因。
长期以来,博山地区的工匠依赖地理资源和市场环境,大多会同时精通陶瓷和琉璃制作工艺。“生产琉璃的炉户们有夏季‘歇伏’的行业传统习俗,这些为避热而停工的工匠们也去就近的陶瓷窑场做工。同一批工匠冬天到琉璃炉场做琉璃,夏天又到陶瓷窑场做陶瓷,年复一年,不曾间断。这种跨陶瓷琉璃行业游动‘做活’是淄博琉璃匠人们特有的行业性习惯,客观上就把琉璃的工艺和色彩元素带到陶瓷烧制上来。淄博琉璃与陶瓷相互影响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多种多样,不仅体现在题材、风格、表现方式、审美情趣,同时还体现在改进及改进后所呈现出的艺术效果,艺术交融所形成的创新是淄博陶瓷与琉璃发展的一种模式探究。”[14]可以猜想,宋朝时期的博山陶瓷匠人在制作色釉的过程中,发现色釉也可以单独制作成品,加上当时琉璃制作在全国已经相当普及,所以他们在这一时期开始制作琉璃也是有可能的。
综合以上论述,将博山琉璃作坊遗址出土的琉璃制品的生产年代定为两宋时期,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
文献与科技检测的双重佐证
除实物自证外,众多史料的记载也对博山琉璃起源于元末明初一说意见相左。如孙廷铨在《颜山杂记》中记载:“余家自洪武垛籍,所领内官监青帘世业也。维国家营建郊坛飨殿,则执治其棂扉帘幌之事而鳞次之。琉璃品映,上彻罘罳,义取乎青象穹苍,答玄贶也。隶籍内廷,班匠事焉,故世执之也。”[9]46
明代宫廷设内官监,主要负责掌管木、石、瓦等10个作坊,以及米盐库、营造库等,其职能主要是营造宫室、陵墓等[15]。当时内官监管理的工匠有两种,一种是担负营建宫殿之类的苦役,这部分人以囚犯为主;另一种是供役工匠,根据不同职业,可以分为人籍、军籍、医籍、匠籍等。一旦确定身份,则必须世代承其役,不能随意改行。供役工匠即指入了匠籍的工匠,又可分为“住坐”和“轮班”两种。住坐匠需常年在宫中服役;轮班匠即上文所说“班匠事焉”的“班匠”,主要从全国各地征调入宫服役。孙廷铨祖上隶属于内廷的工匠,其始祖孙克让就是内官监的青帘匠,主要负责为朝廷生产珠灯、青帘等琉璃制品。青帘是用水晶色的琉璃料,以氧化钴(回青)为着色剂,制成蓝色管形珠,串成帘子,专门悬挂于皇室“郊坛”或“清庙”等尊崇之处,以其颜色象征青天,显其尊贵,可以营造出幽深玄妙的气氛[2]234。
从以上资料分析,博山孙氏家族在洪武年间就为朝廷贡奉琉璃制品,且是专用于国家祭祀场所和大典仪式中,说明他们制作的同类作品应该是当时全国质量最好的,否则不会被朝廷选用。再结合其时间为洪武年间,他们的琉璃制品已经做到全国最好,按照行业发展规律,前面应该有一个较长的发展期。所以博山琉璃的起源应该比元末明初要早。琉璃研究学者张维用更是明确指出:“在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古代社会,一个行业发展到如此规模,绝非短时间内所能达到的。元代存在不足百年,颜神镇玻璃业或许在金代甚至北宋时就已出现。”[16]
朱晓丽在《中国古代珠子》一书第十一章第五节“博山的琉璃珠和明代用于海上贸易的珠子”中曾提及博山琉璃的相关情况:“这些珠子(指博山地区生产的琉璃珠,作者注)在现今东南亚如菲律宾等国家时有出土,从数量看,南宋以前是印度生产的‘印度—太平洋珠’占优势,至少从南宋开始,中国的博山琉璃珠与印度的珠子平分了菲律宾的珠子市场。”[17]该文指出,在南宋或以前,博山地区不仅已经开始生产琉璃,且制作的琉璃珠已经销售到海外。这是第一次对博山琉璃起源于元末明初之说进行否定。
此后数年中,不少论著在提到博山琉璃起源时,均对元末明初说提出过质疑,如杨伯达在考证遗址和相关器物后说道:“一九八二年此地发现了元末明初的玻璃炉址,说明该镇玻璃制造业始创年代很早,曾闻博山琉璃业始于宋,看来也是不无道理的。”[18]李灵枝在《博山琉璃工艺变迁研究》中评述:“根据遗址内展现的琉璃生产规模,产品质量、技术来看,元末明初博山制作琉璃的水平已经十分高超了,在这之前肯定有较长时期的经验积累和技术水平提高的阶段……博山在宋代已经是琉璃生产基地之一了。”[19]
2024年5月10日,中日“博山古琉璃研究”学术交流研讨会在淄博举行,来自日本和国内北京大学和淄博本地专家学者20余人参会。这次研讨会中,国际著名考古学研究机构——日本独立行政法人文化财机构奈良文化财研究所的田村朋美研究员通过对中国博山地区、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地区、日本北海道地区出土的古代玻璃珠进行成分分析,指出北海道地区出土部分古玻璃珠的铅同位素比值与中国山东半岛内的矿床边界附近相似。通过对博山琉璃作坊遗址与日本惠香竖穴群遗址发现的古代琉璃制品进行有损检测与对比分析检测数据显示,两地琉璃的化学成分均属于K2O-PbO-SiO2系统,并含有一定量的CaO成分,二者特征极为相似,因此推测12至17世纪北海道出土的玻璃珠可能是从博山进口过去的产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崔剑锋指出,从金代开始,颜神镇就开始成为中国玻璃制作的中心。其早期玻璃产品主要以小件器物为主,颜色以天蓝色和乳白色为主。这些分析结果与《颜山杂记》中的配方非常接近,证实了该工艺可以上溯至金元时代。同时,在许多重要的遗址考古中都发现了与博山类似的玻璃产品。特别是“南海一号”沉船的玻璃,经过有损分析,发现其显微结构中有萤石残留,说明这类钾钙玻璃很可能产自淄博博山地区[20]。
这次研讨会明确将博山琉璃起源前推至金代(南宋)或更早,较元末明初说提早约200年,为其起源研究提供了实物与科技检测的双重支撑。这种历史性的认知突破,凸显了跨学科研究对工艺史重构的重要价值。
结束语:跨学科视野下的起源重构
综上实物、文献及科技考古数据,无论是《淄博元末明初琉璃作坊遗址》一文的开放式结尾、该遗址出土器物的外形及成分分析,还是相关史料的资证与鉴定,都较为明确地表明博山琉璃起源要早于元末明初。尤为重要的是,结合日本惠香竖穴群所具有的明确考古学断代背景,可以判定这批博山琉璃制品的埋藏时间下限不晚于12至13世纪。这一关键时间节点,为追溯博山琉璃生产的年代上限提供了可靠的交叉断代依据。本研究认为,金代山东地区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与发达的手工业基础,为博山琉璃业的兴起与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历史条件。正是在此期间,博山的琉璃制造工艺已达到相当水平,具备了跨区域文化交流与贸易输出的能力。因此,将博山琉璃作坊的始创年代笼统定为“元末明初”的传统观点亟待修正,其肇始时间应不晚于金代。
作者简介:
怀康,山东理工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陶瓷》主编;
李福源,博山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淄博市民俗文化研究会理事,齐文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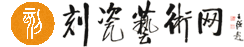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 37039002000142号
鲁公网安备 3703900200014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