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夏,有幸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艺术人才项目——刻瓷技艺创新人才培训,在齐鲁大地,热情淄博学习刻瓷技艺。在当代工艺美术的发展中,“创新”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反复强调的前提。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创作实践,传统工艺似乎都需要通过“创新”来证明自身的现实价值。刻瓷亦是如此。
长期以来,传统工艺不断被放置在“如何创新”的话题之中。然而,对我而言,真正开始反思刻瓷创新这一问题,并不是在阅读相关理论时,而是在一次次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在刻刀落下又停住的瞬间,慢慢形成的。
在参加刻瓷技艺培训以前,我对刻瓷的理解,其实与多数创作者并无太大不同,甚至算不得上有深入的了解。因此对于刻瓷的创新发展,也陷入了仅仅只是思考如何在传统中做出“变化”。在以往大多数的创新途径中,往往意味着题材是否更新,画面是否复杂,形式是否与以往有所区别。在创作时,我也习惯性地以最终呈现的图像作为判断依据,关心作品是否完整,是否“好看”,是否容易被理解。这种思路在很多时候并非没有意义,但当我真正投入到刻瓷的操作过程中时,却逐渐感受到它的局限。
刻瓷是一种几乎不给创作者留下任何退路的技艺。刻刀在釉面上的每一次落点,都会留下清晰而不可逆的痕迹。线条一旦形成,便无法被覆盖或修改。这种特性,使我在创作中不得不反复停顿、判断,甚至在某些瞬间产生犹豫。有时,刻刀悬停在瓷器表面,甚至能够意识到,接下来的这一刀,并不仅仅关系到画面的某一处细节,而会影响整体的节奏与气息。
也正是在这些看似缓慢,甚至略显迟疑的过程中,我开始真正意识到刻瓷的重心并不完全在于“刻出了什么”。更多的时候,我是在与工具和材料进行一种持续的对话。釉面的硬度、刻刀的反馈、手部力量的变化,都会不断影响我的判断。瓷器表面的刻痕并不是事先完全设定好的,而是在刻划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图像并非被简单地“转移”到瓷器表面之上,而是在一次次操作中被生成出来。
随着创作经验的积累,我越来越注意到刻痕本身的意义。刻痕不仅是构成图像的线条,更是创作过程的直接记录。它包含了力量的轻重变化,也保留了节奏的快慢与停顿。有些刻线并不完全规整,甚至带着微妙的不稳定感,但正是这些痕迹,让我清晰地感受到创作当下的身体状态。它们提醒我,这件作品并非只存在于完成的那一刻,而是凝结了一个持续发生的过程。
然而,在现有的评价体系中,刻瓷往往被放置在以绘画或雕刻为参照的标准之中。作品完成度是否高、画面是否清晰、线条是否流畅,常常成为重要的判断依据。在这样的标准下,刻痕很容易被视为服务于图像效果的技术手段,其在创作过程中所形成的痕迹及所蕴含的表达价值,则容易被忽略。在实际创作中,我也曾不自觉地被这种标准牵引,试图让刻痕“看起来更像画”,却在过程中感受到一种隐约的失衡。
正是在不断的尝试与反思中,我逐渐开始调整自己的创作重心。我不再急于追求画面结果的完整,而是更加关注刻瓷的生成过程本身。刻刀如何行进,线条如何在器物表面展开,节奏如何在不断变化中形成整体结构,这些问题逐渐成为我创作中真正关心的部分。当关注点从结果转向过程,刻瓷的创作体验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因此,我更愿意将刻瓷的创新理解为一种方法层面的转向,而非单纯的形式更新。创新不一定体现在“刻了什么新的内容”,而可以体现在“如何去刻”。当我开始从这一角度重新理解刻瓷时,创新不再是一种外在的要求,而成为创作过程中自然生成的结果。
这种理解并不意味着否定传统技法。相反,它建立在对刻瓷长期训练与反复实践的尊重之上。刻瓷的价值,并不在于不断更换外在形式,而在于其技艺方法在不同创作语境中持续发挥作用的能力。对我而言,刻瓷创新并不是一个需要迅速给出答案的问题,而是一种在创作中不断被修正、被深化的理解。或许,刻瓷的当代发展并不必然依赖于剧烈的形式变化,而可以通过对技艺过程、刻痕语言以及创作方式的重新认识,在延续中缓慢展开。这种不急于证明自身的变化方式,也许正是我在个人创作实践中,越来越愿意坚持的一条路径。
最后,对在刻瓷技艺培训和学习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们表示感谢,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对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致以诚挚的谢意。
顺颂文祺。
肖静媚,江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景德镇市美术家协会会员。本硕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个⼈创作涉及陶瓷艺术设计、装饰设计,作品多次⼊选国家级省级⼤展,获第⼗⼆届中国陶瓷艺术⼤展银奖,作品多次被江⻄省⼯艺美术馆及私⼈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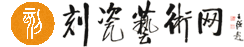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 37039002000142号
鲁公网安备 37039002000142号